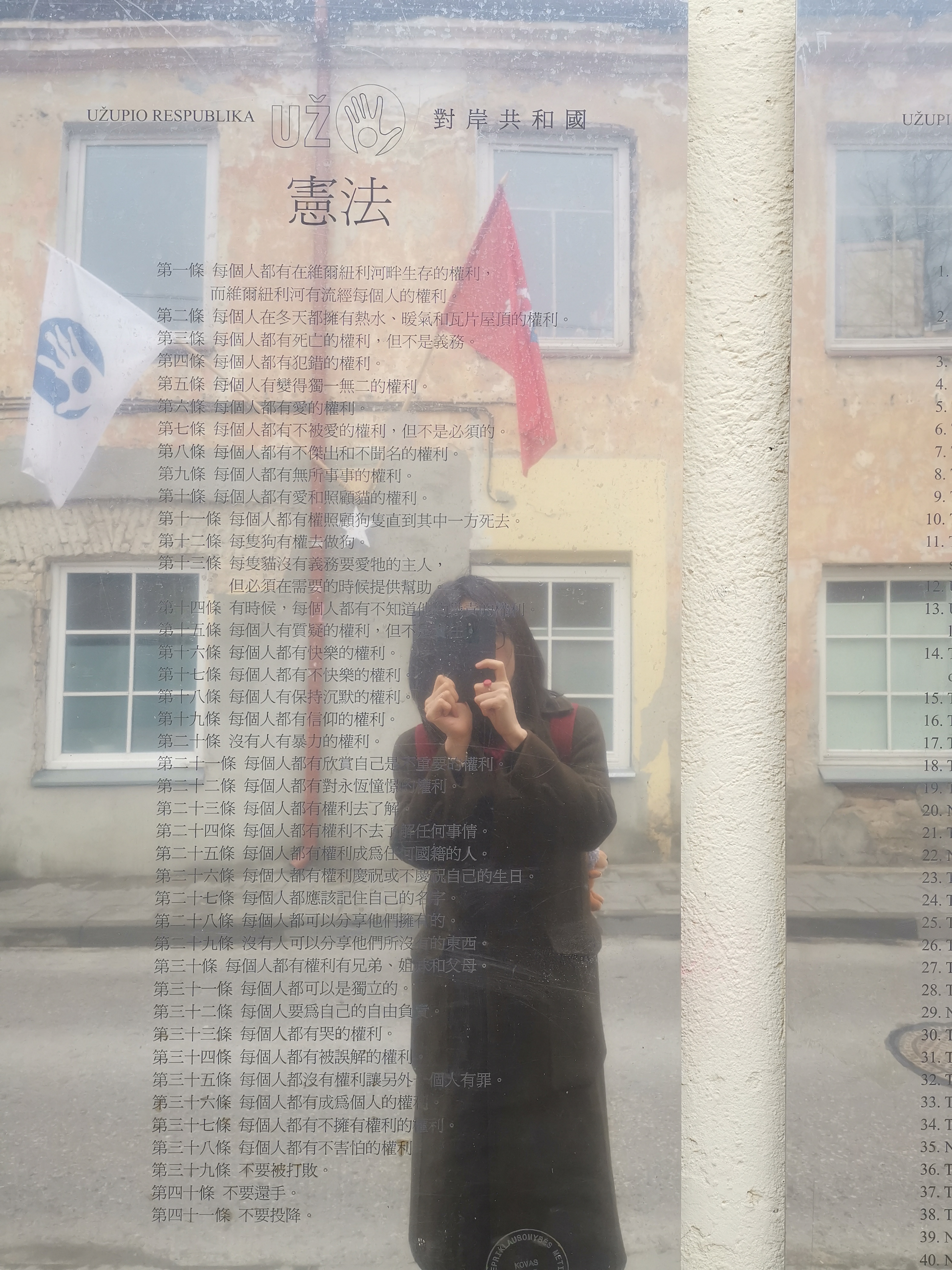记得3月18号公司宣布遣散员工回家工作的通知刚出,Emil告诉Ivan去暂停每周的统计小组学习,Ivan询问是否暂定5月恢复,Emil说: cancel it, it is most likely that we have to stay at home for at least three months. Emil是对的,在家办公的日子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,夏至已至,我们还是没有回去上班。但他还是太乐观了,谁能想到,这爆发的疫情,彻底改变了我习惯了的一套工作方式。无论是否出于保障员工健康的考虑,还是只是出于节省开支,在英国政府逐步放宽种种隔离限制的环境下,公司还是放出年底之前员工不得回去上班的信号。我之前以为这三个月的“不正常”只是暂时状态,没想到,这种隔离在家的生活成了“新常态”。
早上不再会有在地铁上的晨读,取而代之的是在家里铺着垫子健身的挥汗如雨;不再会有在公司茶水间的早餐闲扯,取而代之的是在千篇一律的燕麦粥配百家讲坛的音频故事;中午不再会有在健身房的争分夺秒,取而代之的一整天坐在桌前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邮件开电话会议;傍晚不再会有期待下班的心情和在超市挑选晚餐食材的纠结,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茫然和自虐式的健身。生活和工作没有了明显的界限,个体的外在属性与内在属性丧失了意义 …